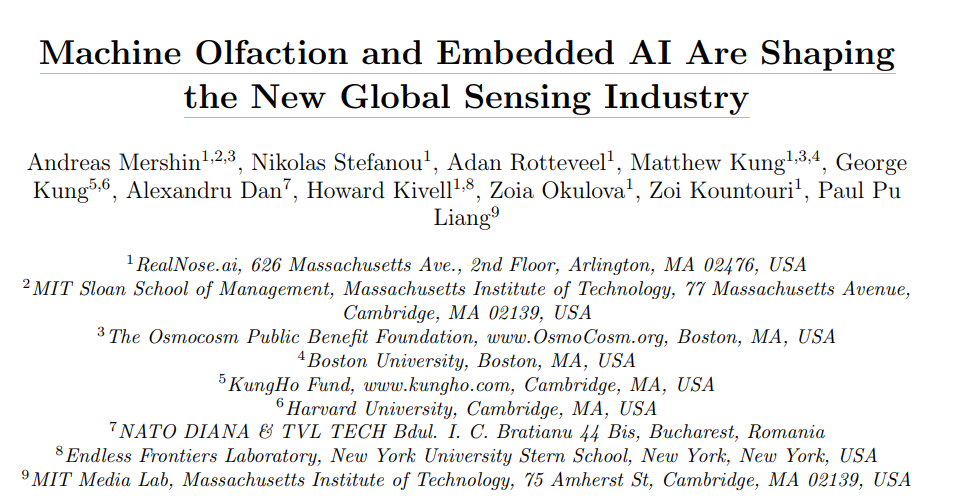机器嗅觉正迅速崛起为一种变革性能力,其应用范围涵盖无创医疗诊断、工业监测、农业以及安全与国防领域。近期在稳定哺乳动物嗅觉受体并将其集成到生物光子和生物电子系统方面取得的进展,已能实现近乎单分子分辨率的检测,从而使机器能力与训练有素的探测犬相媲美。随着该技术与多模态人工智能及蕴含嵌入式人工智能的分布式传感器网络相融合,它为当前由机器视觉和听觉主导的传感生态系统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生物化学层面。本综述与行业路线图审视了机器嗅觉的科学基础、技术前沿及战略应用,论证了我们正见证一个带来全球化学传感基础设施的新兴产业的崛起。我们涵盖了代表性的工业、军事和消费类应用,并探讨了由此产生的一些伦理和法律问题。我们发现,机器嗅觉有望催生一个覆盖全球的分子感知技术层,并有可能通过气味在健康、安全和环境传感领域催生巨大的新兴市场。
在整个进化过程中,生命一直依赖于通过空气和水交换化学信息。嗅觉,即嗅觉感官,使生物体能够检测微量的挥发性化合物并据此采取行动,引导它们寻找食物和配偶,甚至赋予它们通过嗅闻来检测人类疾病的能力[1]。虽然机器视觉和听觉现已能与人类的眼睛和耳朵相媲美,但我们的技术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匹敌鼻子[2]。生物嗅觉的核心是一种分子匹配和模式识别的非凡能力:称为气味剂的小分子(通常原子量低于350)以高度特异性与更大的膜结合受体(通常分子量为30,000)结合,触发甚至整个生物体对极其微小的化学线索的行为反应。传统分析系统,如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液相色谱-质谱联用(LC-MS)以及涉及各种传感器的气味指纹图谱方法,常被尝试用作“鼻子”。这些系统传统上使用金属氧化物传感器,以及干涉测量、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石英晶体微天平(QCM)或太赫兹时域光谱(THz-TDS)平台[3–7],并在实验室条件下长期实现了卓越的灵敏度,但无一能造出具有情境细微差别、特异性、泛化能力或速度的机器嗅觉仪,以真正模仿生物嗅觉感官及使用它的神经系统的能力。
两个关键障碍阻碍了机器嗅觉加入机器视觉和听觉的行列:1) “检测极限”,即机器嗅觉仪无法可靠响应单分子事件;2) “识别极限”,即在动态波动的背景噪声中解码混合气味羽流中复杂气味特征的能力。这两个障碍正在被克服。一项突破是成功将稳定的哺乳动物嗅觉受体集成到光子和电子器件中[8–11]。这些系统与现代人工智能(包括深度神经网络和大语言模型[12–15])相结合,在实际气味识别方面展现出前景。诸如DARPA的“狗鼻子”和“真鼻子”项目[16–18]推动了这一转变,证明了将生物受体嵌入设备是有效的。近期的进展有望使生物机器鼻子能够检测尿液中的疾病特征、在野外嗅出化学威胁,并能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由飘散气味剂带来的数千种气味[1, 19–21]。
随着这些系统的成熟,基于受体的传感器、传感器阵列和人工智能分类器正汇聚成可部署的平台。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证实了在工程膜中实现单分子检测、强大的嗅觉分类以及在医疗保健、农业和国防领域的应用[22, 23]。因此,机器嗅觉正迅速从一个被忽视的领域转变为智能传感的基础层,有望在下一代传感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中补充并在某些方面超越光和声传感。